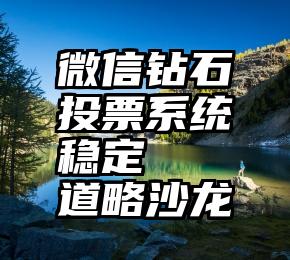.jpg)
《白人的薪水:族群与英国劳动阶级的逐步形成》,[美]彼得·R.吉尔格著,朱锐、李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320页,65.00元
2022年4月,《LX1的别离》(Hillbilly Elegy)的译者、正在出选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的詹姆斯·戴维·Hradeck(J. D. Vance)接受了前总统奥巴马的在政治上背书——虽然几年以前,Hradeck还曾文章奥巴马是招人讨厌的白痴,容忍朋友在聊天时将奥巴马与尼克松和希特勒较之,但较之于后期选举的大局,这点陈年宿怨无关紧要。Hradeck与奥巴马二人势不两立的场面,象征着2016年总统大选年来在英国盛行的下层白人女性诗歌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在政治上高度。而此流派致力于呈现出英裔劳动阶级(white working-class)的生活经济危机,将2016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的失败和共和党的绒兰民粹主义化归咎于下层白人女性的失落,认为两党菁英都忽视了英国去城市化进程中真正受到损害的人群——低教育水平、低收入的白人。2016年《LX1的别离》大获成功后,下层白人女性诗歌创作在英国新闻报道、现代文学和影视剧中呈现出井喷之势,成品质量参差不齐,但常常同时混合着社会批判与下层白人女性的离愁。
英裔建筑工人垄断了英国亚文化中的劳动阶级形像
下层白人女性诗歌创作或许是2016年年来英国公共舆论中最受关注的表现手法之一,但是,而此表现手法在英国发展史上并并非头一回盛行了。下层白人的苦难曾是英国南部现代文学的核心表现手法,在英国新闻报道和社会文章中,白人女性经济危机的主题几乎每二三十年就会涌现一次。区别在于,2016年年来的而此波诗歌创作将下层白人女性的经历与上世纪七十年代年来英国的去城市化联系起来。而此次,下层白人女性的形像既并非芝加哥养猪场里的东欧移民,也并非被沙尘逐出摘星的俄克拉何马小农,而要被资本主义分配秩序和资产阶级菁英文化双重排外的雇佣建筑工人。她们工作辛劳,所得甚少,无力与产业转移的大潮对抗,只能沉湎于英国劳动阶级黄金时代的往日短蕊之中,将生活的酸楚与怨懑发泄在更为弱势的外来社会群体身上。——而此形像在英国发展史中有原型吗?彼得·吉尔格的《白人的薪水:族群与英国劳动阶级的逐步形成》正是这样一部穷本追根溯源之作。两本书虽然第一卷于1991年,研究的主要也是1860年内战前英国英裔建筑工人的族群观念,却对当下英国劳动阶级面临的痛点做出了巧妙的回应。
吉尔格在两本书中试图回答困扰英国外劳史研究已久的痛点:作为一个拥有发达的工业基础和悠久的外劳运动发展史的国家,英国为何始终难以逐步形成统一的劳动阶级认同?为何英国庞大的建筑工人社会群体常常被族群、异性恋、出生地的高墙割裂?不仅如此,在亚文化和在政治上动员的话语中,劳动阶级的形像常常被不切实际地赋予了太多的族群和异性恋预设——每当提到英国建筑工人(working men),人们脑海中常常想当然地浮现出一个成年白人男子的形像,虽然在许多行业尤其是下层行业中,白人、拉美裔、华裔和女性劳动者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出白人女性。在保守派的在政治上辞汇中,保护建筑工人的自身利益指的常常就是英裔建筑工人的自身利益,而其它社会群体的自身利益会被称为特定自身利益。甚至在德国大众消费市场需求文化中,普通消费市场需求者通常指的也是白人家庭成员,德国大众消费市场需求品的结构设计都是如前所述白人家庭成员的消费市场需求习惯,只有在满足了白人家庭成员的消费市场需求市场需求后,商家才会为其它族群结构设计符合她们市场需求的特定商品。
英裔建筑工人对其它族群的排外因何而起?是如前所述族群间的仇恨吗?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大部分英裔人对少数族群一无所知。《白人的薪水》第一章首章,就是译者吉尔格的思想自传:吉尔格成长于二十世纪后期伊利诺伊州的一个犹太裔英国人小城,这个小城属于族群隔离时代所谓的落日镇(sunset town),日落后一切白人都不准在镇上留驻。虽然人们在日常生活几乎不需要跟白人打交道,但白人这个概念却时常被提及——并非现实生活中的白人,并非新闻报道里的民权剑士或是电视上的白人名人,而要抽象的白人社会群体——白人抢走了白人的工作、白人不缴税、白人是危险分子。这些关于白人的对话并非发生在白人与白人之间,而永远是发生在白人与白人之间。白人谈论白人也并非因为她们真的对华裔社会群体感兴趣,而要为了显得比自己的白人同伴更聪明、更厉害、更有权威。
吉尔格发现,这种对于不在场的白人社会群体的讨论,才是英国白人发展史中的常态。英裔建筑工人之所以执着地将白人排除在外,并并非白人社会群体做了什么,而要因为这种排外对英裔建筑工人本身至关重要。在英国发展史中,白人社会群体和奴隶制的长久存在,为英裔建筑工人提供了一个族群主义的文化抓手,建筑工人将自己定义为白人,以此将自身与不自由不勤奋不聪明的白人奴隶社会群体区别开来,这种族群情绪成为英裔建筑工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英裔建筑工人的族群主义是一种夹杂着仇恨、悲伤和渴望的复杂情感,它经常隐匿在阶级话语的背后,混淆我们对外劳社会群体身份的认知。而资本家对英裔建筑工人的族群主义话语乐见其成,因为它削弱了不同族群建筑工人间的团结,又分散了劳动者对于不公正的经济分配秩序的注意力。
英国建筑工人白人身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英国革命时期
除第一章深刻的自我反思和第八章的总结之外,两本书的主体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二章至第四章从在政治上文化角度梳理了英国革命前后至内战前英国英裔劳动阶级认同的逐步形成——劳动阶级(working class)为何会被默认是白人?白人身份(whiteness)为何会与建筑工人的阶级认同和在政治上权利联系起来?第五章至第七章则是对英裔建筑工人族群主义具体形态的分析——英裔建筑工人的族群主义如何通过节庆、游艺、歌曲等亚文化形式,被表征为一种劳动阶级文化?在下层建筑工人文化中,不在场的白人如何被塑造为某种刻板印象,最终成为英裔建筑工人生活中习焉不察的元素?
从英国发展史的开端,我们就不难发现,建筑工人而此概念的塑造与劳动者的发展史现实从来就并非同步的。建筑工人(workingman/worker)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是白色的,它的对立面是殖民者眼中懒惰不事生产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虽然世居于此,却不懂得开发这片土地的真正价值。在殖民者看来,只有英裔男人具有开拓土地的智力、勤劳、美德和强壮体力,她们代表着文明,因此,英裔人获得了开发新大陆土地的自然合法性。
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开展,白人逐渐成为北美劳动者社会群体中重要的一分子。在十八世纪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中,黑白杂处是司空见惯的,人们并不会简单地将白人等同于奴隶,将白人等同于雇佣建筑工人。十八世纪北美的经济现实与文化观念也与今日不同,社会上仍然存在大量白人契约奴工、债务奴隶、被迫劳动的犯人、不领薪水的学徒,而在当时的族群观念中,德国人等族群还不被看作百分之百的白人,因此,德国大众很难在白人与奴隶之间划上简单的等号。
建筑工人概念开始带上强烈的白人族群色彩始于英国革命时期。北美革命者称自己为自由人,实际上鼓励了自雇的白人劳动者与白人奴隶对立的观念。革命期间的在政治上话语反复利用奴隶意象来唤起殖民地人对于被英国在政治上奴役的恐惧,其动员效果正仰赖于白人对目下所见的黑奴生存状态的恐惧。当然,革命一代也曾因为自身被奴役的状态而产生了对黑奴的同情,甚至提出废奴的主张,但是,这种团结是短暂的。事实证明,优势社会群体只有在社会秩序极端动荡、不安全感笼罩的情况下,才会对弱势社会群体产生短暂的、虚幻的共情。在革命结束后,这种如前所述被奴役的黑白团结很快被一种白人共和主义的话语取代:只有白人具有为自身自由奋战的基因,而白人的天生奴性导致了她们被奴役,并且绝不会奋起反抗。
英裔建筑工人担心的被奴役并并非真正的卖身为奴,而要一种经济依附状态:缺少独立的财产和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和经济安排上受制于人——也就是长期被雇佣的状态。杰克逊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雇佣变得越来越普遍,因此,英裔建筑工人发明了众多的区隔用词,来突出自身与白人奴隶间的差异:例如,将自身称为帮手(help)而非仆人(servant),称呼雇主为老板(boss)而非主人(master)。在杰克逊时代,女性气概被构造为白人外劳阶级自我认同的核心要件,自由人(freeman)这个称呼对于白人外劳阶级具有双层含义,它既暗示着她们作为受雇佣者的依附状态是暂时的,也明示了她们与白人奴隶的区别。杰克逊民主的发展为而此区别增加了共和主义的视角:一个穷苦的白人外劳可能在经济上受制于人,但仍然因为具有投票权而成为共和国的公民,从而自豪地证成他自由人的身份。换句话说,在英裔女性建筑工人的自我认同中,白人女性自由这三个词本质上是一个整体。
英裔建筑工人也塑造了十九世纪亚文化中的白人形像
既然英裔建筑工人是自由独立女性气概和公民精神的化身,白人就必须被塑造成另一种形像。虽然在在政治上生活中,法律上的白人奴隶制已经被内战终结,但族群主义在亚文化中以另一种面貌存续下来。在十九世纪的城市化过程中,英裔建筑工人文化塑造的自身形像恰好迎合了资本主义劳动纪律对建筑工人的规训。新生的工业生产秩序要求劳动者勤奋专一、热爱工作、有时间观念、能够约束欲望、推迟满足与享乐。当英裔建筑工人不得不接受这些劳动纪律时,她们将自身对于前工业时代生活的怀恋移情到白人身上,将白人想象成那个纵情酒色、懒散闲适的曾的自己。用发展史学家乔治·拉威克的话说,十九世纪的英裔建筑工人在想象白人生活时,就像一个改过自新的罪人遇到了从前一同纵情享乐的朋友一般。在英裔建筑工人的想象中,白人是她们既鄙视又怀念的前工业时代的化身。
这种混合了阶级与族群要素的文化想象通过十九世纪的德国大众娱乐普及到了劳动阶级之中。十九世纪下层建筑工人中最盛行的舞台表演形式之一是扮黑脸(blackface)和白人歌曲(coon songs),这些表演在形式上模仿白人,但其主题并并非南方白人奴隶的悲惨生活。这些涂成黑脸的白人演员可能扮演各种边缘的角色和有争议的表现手法,她们是花花公子、懒汉、浪荡子甚至异教徒,她们抨击政客、讽刺唯利是图的商人、嘲笑宗教卫道士,扮黑脸可以使用高雅文化中无法出现的粗俗语言和性暗示——这是一种下层英裔建筑工人借白人之口、以戏谑而安全的方式冒犯资本主义秩序的表演,它表达的实际上是英裔建筑工人自身时刻感受却又无法明言的失落与愤怒。这类表演形式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下:自革命以后,真正的白人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出了白人的庆典,而在工业秩序的压抑下,白人表演者只能使用白人形像来表征自身文化记忆中狂欢与放纵的角色。而在扮白人表演中,白人表演者常常又要时刻跳脱出来,提醒观众她们只是扮作白人的白人,唤起白人观众对自身白人身份的庆幸感觉。
.jpg) 1850年代的在政治上漫画:爱尔兰和德国移民偷走了英国人的投票箱。
1850年代的在政治上漫画:爱尔兰和德国移民偷走了英国人的投票箱。研究发展史上的白人身份能帮助我们避免认知中的白人盲区
在方法论上,吉尔格的研究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新社会史、新外劳史兴起后的第二代新外劳史研究。与赫伯特·古特曼、E. P.汤普森等先驱者一样,吉尔格仍然注目于硬性社会结构的软性文化表征,展现了劳动阶级如何面对资产阶级霸权,在不利的发展史境遇中积极创造自身的文化形式,却又时刻被社会阶级结构所局限。与上一代新外劳史研究者较之,吉尔格的研究没有集中在被压迫者如何反抗压迫的老调上,而要选择关注下层英裔建筑工人主动拥抱族群主义、通过塑造白人他者来为自身谋求心理、经济和在政治上补偿的行为。无论从白人史还是外劳史角度,吉尔格的白人身份研究都极具新意,开启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在理论定位上,白人身份研究可以对标异性恋研究中的女性气质研究或是资本主义史中的资产阶级研究。第五章和第六章使用的大量音乐材料也丰富了外劳研究的史料类型,将更为下层的视角带入了发展史学家的视野。
自2016年总统大选以后,随着民粹主义主义、族群主义、厌女主义等右翼思想在英国社会再次沉渣泛起,英国研究界常常陷入当代英国的社会问题到底是经济问题还是文化问题的争论之中。如果辩论的参与者读过吉尔格的研究,或许就会意识到这种经济文化两分法的虚妄。人们当然可以把族群和异性恋压迫看作阶级压迫的延续,英国白人的发展史和现实困境当然也根源于她们手中经济力量的不足,但这并不表示,解决了经济问题,所有族群和其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相反,将一切族群问题简化为阶级问题,常常会给研究者带来一种自身思想格外深刻的幻觉:遗憾的是,有时候马克思主义者更容易落入而此陷阱,她们可能会认为阶级比其它社会领域更为根本和实在,却忽略了发展史上的阶级划分本身也可能带有族群与异性恋的先天标签。研究者自以为站在中立的立场,实际上却是落入了认知的白人盲区之中。用吉尔格书中的话说,族群主义是植根于阶级关系大树上的一棵树枝,若要撼动树根,就必须晃动族群主义的树枝。当我们阅读晚近的下层白人女性诗歌创作时,也应该时常警醒自己:这些故事中描绘的英国劳动阶级的黄金年代到底是谁的黄金年代?为何英国去城市化的故事常常被一部分人的故事所代表?谁在塑造当代英国下层白人经济危机的神话?也许只有借用吉尔格等发展史学家的作品,从更长时段的视角来观察,我们才能分辨当代不同的下层白人女性诗歌创作中,社会良心与在政治上企图各占几分成色。
 百万个冷知识
百万个冷知识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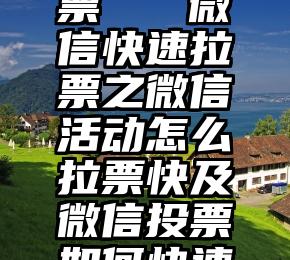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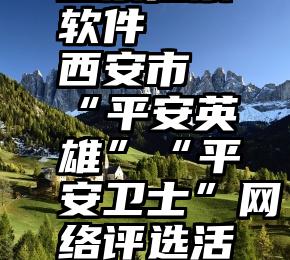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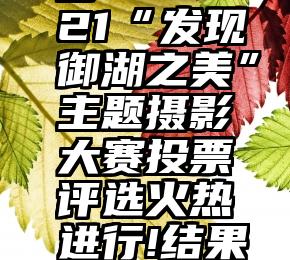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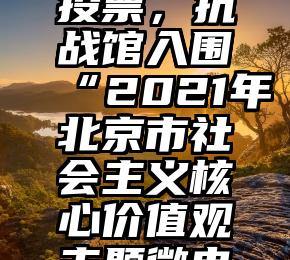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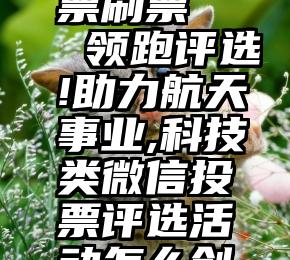
.jpg)